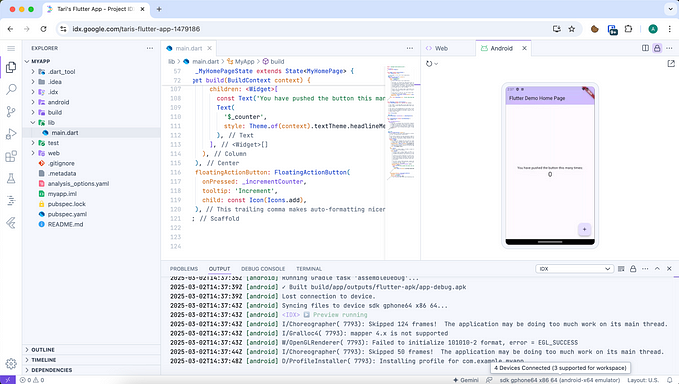對於理想人生的渴望、追尋有意義的人生,是人類的本能。從職能科學的角度來說,有意義的人生,便是透過做自己想做的事(doing)、感受自己真實的存在(being),活成自己最想成為的樣子(becoming)。(延伸閱讀_Doing, Being, Becoming.)
提出Doing, being, becoming (Wilcock, 1999)概念的學者,後來又在這個基礎之上,加上了「歸屬(belonging)」的概念:
Doing, being, becoming, and belonging are the means to both survival needs and health and well-being (Wilcock, 2006). 做想做的事,真實的存在,成為自己最想成為的樣子,找到自己的歸屬,是人類生存及安適的媒介。
在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中,人類的社會需求,包含了被他人接受、以及感覺到歸屬;人,透過與他人的互動,來理解自己的存在與價值,進而感受到滿足,因此感受到歸屬,能讓人類的行爲產生「意義」,讓活動成為職能。
歸屬感其實就是一種身份的認同(identity),一群人對共同的價值感產生共鳴、對於一個身份產生情感的連結,這種彼此認同的感覺,就是一種歸屬。讓人感到歸屬的群體可大可小,學校、世代、種族、性別,不論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團體界線,通常我們都可以找到一個安放自己角色的位置。但我們今天要談的,是一個相當大規模,而且有點敏感、有時候有點模糊的群體認同 — 國家的認同(national identity)。
人類的文化相當複雜,在一個國家地區中,人們可能會具有不同的身份認同。一篇2020年的文章中提到,國家認同的概念,有兩種不同的極端,一種是民族認同(ethnic identity)另一種是公民(civic identity)。民族認同(ethnic identity)是對於民族、血脈(blood)所產生的認同感,中國「漢民族」的認同就是屬於這一類;公民認同(civic identity)則是偏向於人民對於共同價值所產生的認同感,美國、加拿大的國家認同比較偏向這一端 (Mathews, 2020)。
雖然「國家」聽起來是一個很明確的概念,但對某些人來說,理解自己對於「國家」的認同感,是有困難的。在Mathews(2020)的這篇文章中就提到,在香港人的歷史中,他們對於「歸屬於一個國家(belong to a nation)」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。
A “stateless nation” is a political community that lacks a state of its own but consciously self-identities itself “as distinct people with enough cohesion to seek some sort of greater self-government.” (Fong, 2019)不被承認的國家,是指一個有自我意識的、缺乏國家定位的政治群體,當中的人們具備足夠的凝聚力,去尋求某種形式的自治。
另一篇2019年的文章中點出,對於偏向支持公民認同(civic identity)的人來說,「國家」的概念,並不一定需要有共同民族血脈為基礎。我們從最近香港的社會運動就可以看出,許多年輕一輩的香港人無法接受「中國人」這樣的民族認同(ethnic identity),並且逐漸發展出一個新的、偏向公民認同(civic identity)的「國家」認同:香港人(HongKonger)。
對於香港人來說,「香港人(HongKonger)」的認同所代表的,並不只是一個國家的界線、民族的定義,而是他們對於自由民主更崇高的共同價值。
國家認同與職能正義
人們有自由和權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、產生自我認同及歸屬,進而獲得人生的意義,這就是職能的正義(occupational justice)。
在街上抗爭的香港人們,當他們主觀的國家認同,因為外在的社會環境、歷史、文化、政治因素被否定,長期感到被孤立、缺乏自我認同及歸屬,這便是族群(population)階層的職能系統,由於職能的剝奪(occupational deprivation)而產生了職能的疏離(occupational alienation),是一種職能的不正義(occupational injustice)。(延伸閱讀_職能正義、超越個體的職能定義。)
目前香港人們所面臨的,當然不只是職能不正義的問題,背後涉及的是更複雜的國際政治、經濟、法律和人權的議題。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在5月28日通過,授權人大常委,將嚴重影響人權的《香港國安法》,加入《香港基本法》第18條的附件三。香港國安法,將會影響到人民因為擔心被扣上「分裂國家、顛覆國政權」的罪名,而被限制的言論、集會、思想等等的自由。
社會正義、人權、和職能正義,是彼此緊密相關的,職能的不正義、人權的打壓,無疑地會長期、嚴重影響到人們各個層面的健康。Wilcock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,職能治療重視的,並不只是「回復健康」,而是更近一步初級預防(primary prevention)的「健康促進」。要做到在疾病發生前的初級預防,就必須要了解社會中各種可能影響人類健康的因素。
目前香港的情勢我們雖然無能為力,但只要你在乎人權,關心所有為職能而存在的個體,你就應該要試著了解及思考整個香港經驗背後的意義。所有人都應該要能夠自由地活著。
References:
Ann A. Wilcock (2007). Occupation and Health: Are They One and the Same?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, 14:1, 3–8.
Ann A. Wilcock (2006). Occupational-Focused Approach to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and Well-Being. An Occupational Perspective of Health, 2nd edition (312–321). Thorofare, NJ: Slack Inc; 2006.
Gordon Mathews (2020). The Hong Kong protests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- National identity and what it means.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, 0(0),1–6.
Brian C.H. Fong (2019). Stateless Nation Within a Nationless State: The Political Past, Present, and Future of Hongkongers, 1949–2019. Nationa and Nationalism, 2019, 1–18.